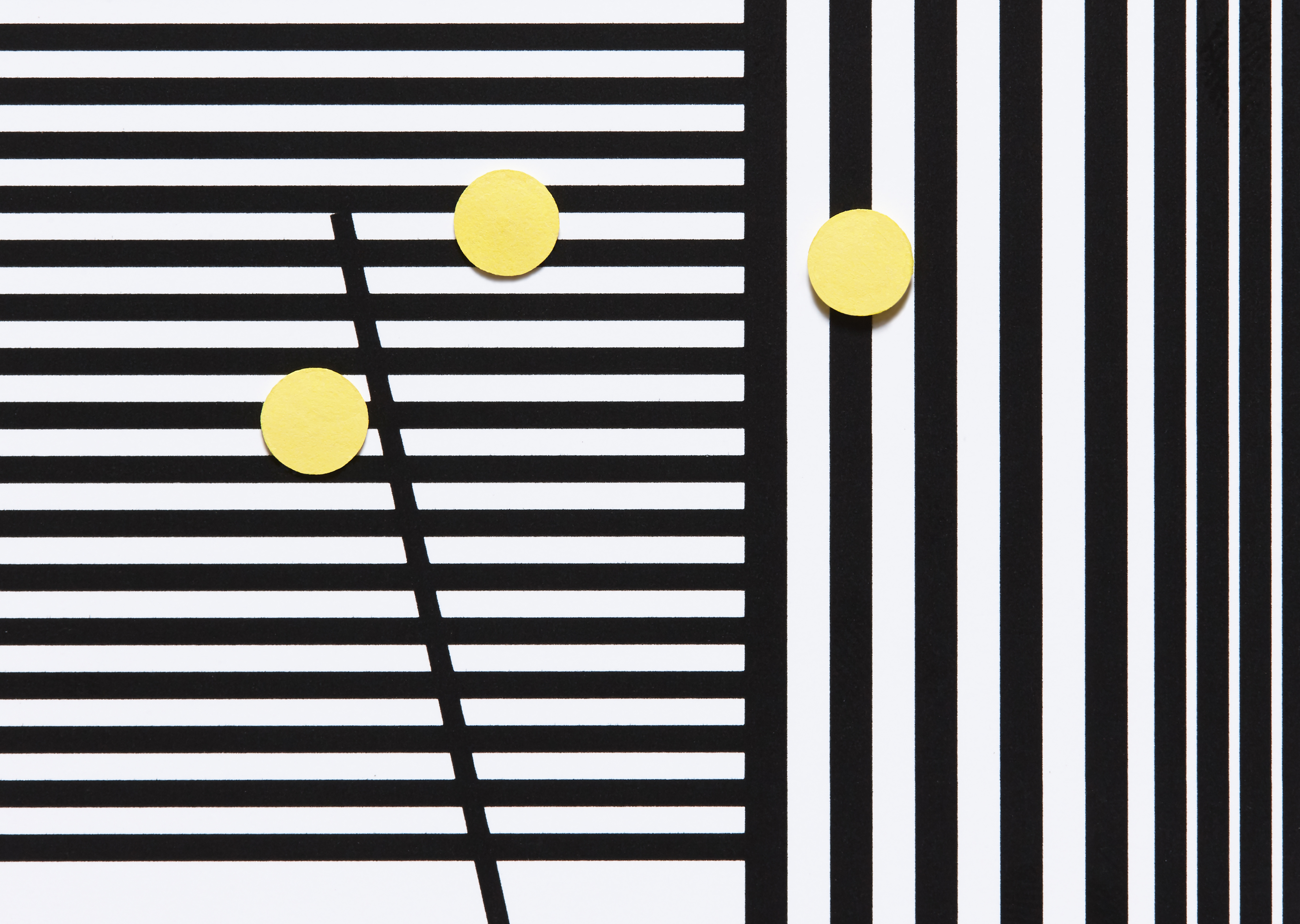蕾丝的故事
我们的记忆,我们与岁月共度的时间,我们在生活中有过的所有感受,最终都会写入我们的作品中,会与一些作品的题材和维度交融。而且,我越来越觉得,设计做成什么样,是由设计师性情或者习惯决定的,甚至有些“宿命论”的意思。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、工作中对整洁都有着严格的要求,那必然在设计中也有相似的追求。同理,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、工作中都很奔放,不讲究细节,那他的设计也大概如此。几乎不太可能会出现生活中的习惯与设计表现完全分裂的状况。
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,在生活中,你是不是一个细致的人?如果你是,那在设计的执行过程中,是不是细致已经做为最基本的标准了,无须特别提醒和注意。我相熟的设计师,像广煜、刘治治,包括我自己,我们所做的设计跟生活中的我们非常相似。我似乎可以做这样一个总结,做设计,基本上就是把自己映射到工作中。你是什么人,就做什么样的设计。
设计师将个性投射到作品上,设计作品因此展现出各式各样的可能性,有的优雅,有的粗狂,有的谨慎,有的大胆……造就这些设计不同的原始素材,都来源于设计师的生活阅历。这些生活阅历成就了你的人设,把你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格,决定你做出选择,这是一种绑定的关系。我们在设计中注入的个性,反应出的作品风格,也会成为我们被客户选择时的标签。客户们在寻找相互认同的合作者,而个性及作品表达方式,就成了客户选择的条件。
当然,我们对生活和个性的理解,也会随着时间的推进发生变化。这些变化,也会影响我们对设计的看法。我以前对女性的、细腻的、敏感的视觉语言是很抗拒的,主要是我无法让自己站在女性化的视角里去体会那种感受,我猜这其中的阻力一方面来自于性别的偏执,另一方面则是不愿走出那个封闭的自我认知。但是,一件小事永远地改变了我。
那一年秋天,我走进了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家小店,那是一家开在广场附近的蕾丝店。起初,我是没打算进去的,因为蕾丝会让我产生眩晕感,让我紧张,我猜很多男性在进入女性内衣店时,都会产生这种紧张和尴尬的感觉。随行的是一对儿男女朋友,男生陪女生进去了,我站在外面愣了一会儿后,发现这家店真的很特别,历史悠久且招牌上的字体和装饰很是讲究。既然,我那两个朋友一时半会儿不想走,那我也就硬着头皮走进了这家店。
里面空间不大,但出售的商品有成千上万种,布置得就像天使的闺房。蕾丝产品被仔细归类放入到不同的抽屉、木格里,像博物馆中的陈列一样整齐。我低头看着不同的蕾丝花边,赞叹着它们的细节和工艺,拿出其中几条放在手里感受质感:轻柔、精巧、泛着微光……视线切换时,突然瞥见柜台后面站着的一个胖胖的老头,他微笑着向我点头,穿着棉质的白衬衫,胡须和头发都打理得非常精致。啊,这位可能是老板吧?我放下手里的蕾丝向他问好,心里暗暗地想:居然是这样一个人在经营这家店啊,他居然是个男的。那时,我在潜意识里觉得,怎么会是个男老板呢?他(一个男的)怎么会做了蕾丝的生意?呃……突然,就在一瞬间,我觉得我好像明白了什么。男的,怎么就不能开蕾丝店了?!我不就在这蕾丝店里逛得很开心吗,我看着手里拿着的精致的蕾丝边,心里给自己打气:走出那一步,不要那么保守了!
很多时候,我们处于一种观念封闭的状态,会嘲笑,会不理解那些与我们观念不同的人。但,随着我们对世界的了解越来越多,眼界越来越开阔,内心也会越来越包容,会一次次地打破边界的限制,自己的感受能力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。
在佛罗伦萨的经历,也催生了我的一组设计:《落花》。这是一套关于花的系列产品,包括三张印着抽象树木的卡片,相配的信封和一些彩色的纸屑。在使用过程中,人们会先拿到一个看上去平庸无奇的彩色信封,打开后取出里面的卡片,这时,彩色的纸屑会跟着卡片一起被带出来,飘落到身上、桌子上、地上,粘在手上,甚至钻进袖子里。掉出来的纸屑跟卡片上印着的花是呼应的,在视觉心理上,就是卡片上的花落在了现实世界中你的手里,地板上。我想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带着伤感和无奈的凄美画面,像是电影里大雪纷飞中两人隔窗相望的时刻,也有连接抽象与真实世界的意味。
这个具有女性化色彩的题材,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。但当它被做出来以后,我的感觉非常好。我知道自己可以尝试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做设计了,我的世界一下就宽阔了许多。《落花》这件作品的创作源于一个人:王尔德——一个钟情于花朵、落日和文学的人。《落花》是为了纪念王尔德,但我没有在作品的描述中提到他,我觉得他不需要被“纪念”,他只是真实地去感受这个世界,并大胆地讲出自己的感受,而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尝试去做的。
人生漫长,设计师的创作之路也一样。不断调整和发现自己内心的渴求,是值得用一辈子去做的事情。而这些人生岁月,都将会写进我们的设计中。